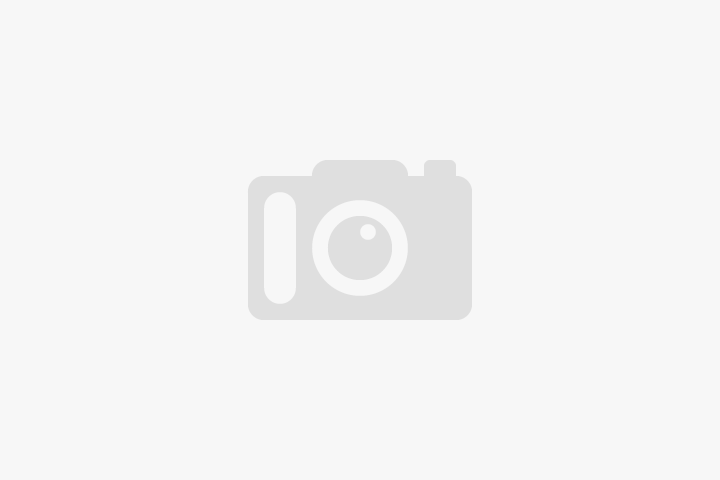微信扫一扫

乌 江 改 道--上辈农民的壮举
道 ▌周继先
乌 江 改 道 图 /文:周继先 润泽田园兴百业,哺滋人类惠千乡。 狂来肆意汹涎液,性起随时造祸殃。 今日改铺宽玉带,当年恶水变琼浆。 源自湘乡羚羊山北麓之乌江,为宁乡四江之一。属湘江二级支流。自西向东全长一百六十里,流经宁乡境内八十二里,终端一头扎进沩江,最终奔向大海。 乌江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作孽不少。 为了让其更好的造福人类,四十八年前(公元 一九七五年)秋收刚一结束,沿河六个公社的两万多名民工在县指挥部的一声号令下,浩浩荡荡开赴乌江改道工地。县指挥部指挥长为当时的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宁乡老革命、老地下党员陶季斌。其时陶正率队在我们东鹜山公社办点,自然这里就成了乌江改道的大本营(下级六个公社分别设立指挥部)。 工地采取互相对调,异地施工的策略,因而六个公社的民工都得带行囊、工具去他乡劳动、食宿。我们大队被安排在河对岸的偕乐桥公社地段,驻地叫荷叶塘。以生产队为单位设食堂,我们队很大,总人口有四百多人,上工地的劳动力就有百多号人。 公社指挥部设在本社双联大队的槐花塘,该地紧挨乌江,对工程便于管理,更能实时实地进行领导。 到达驻地的当天,大家买了几样生活必须品,接着开好床铺,我们一伙六人住宿在袁姓家里的草楼上,本以为柔软保暖,占了先机,可谁知待到冬天炒豆般的雪籽通过瓦缝打到脸上,又冰又痛,结果之前的美好设想仅是个小聪明而已。更有甚者,有个伙计睡梦中滚落到楼下猪栏里,不偏不倚地摔在大母猪背上,惊得那母猪嗷嗷直叫,还被大家笑话。 公社指挥部规定:实行干部(所有国家干部下沉至生产队)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政策,食堂只蒸饭,各自备菜,一次备足三五天的菜,认为天气越来越冷好储存。自然只能带些干菜,酸菜,头批菜吃完后,只能晚上请假回家接菜。这种做法叫作干部民工“一筒公”(“筒公”为盛菜容器)。可“一筒公”的规定没实行多久,问题就来了,餐餐干菜酸菜,民工们消化系统受到破坏,大多火盛、便秘,得频繁地跑厕所,以致造成肛裂便血等病症,闹得大家夜不能寝,备受折磨。白天忘我劳动,晚间还得纷纷去田边河边寻找凉草药缓解症状,情况逐级向上反映,为保健康,促工效,上级视情取消了“一筒公”政策(其实当年也是无奈之举,集体经济困难,家庭经济也糟糕,每劳动日几毛钱,一斤多粮,项项得节约)。不得不改成发动民工自带蔬菜,学校组织师生捐菜,多措并举,队上买油盐还不时地拼出血本,鱼呀肉呀的打打牙祭,民工们的身体好了,自然劳动积极性高了,工效就迅速提高。 当年基建全靠人工,几十里长的战线,除开用炸药爆破新河道石头和坚土外,看不到机械的身影,工程量大,明令要在春汛前开挖出新河道,来年春耕前搞好旧河还田,由新河灌溉农田。工期短导致劳动强度大。每天六点起床,不到七点开工,冬天日短夜长,下午五点半收工,除回食堂用中歺外,其余时间不得擅离工地。 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口号是:高标准、高工效、低消耗完成乌江改道工程。沿江红旗招展,高音喇叭终日叫个不停,县指挥部反复播送毛主席当时发表的两首词:念奴娇《鸟儿问答》和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是为当年最重要的政治学习内容。同时不时召开战地会,陶季斌总指挥长基本每隔三五日就会率领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沿线检查督战,猛促工程进度。 除指挥部的宣传机器外,各大队都架设高音喇叭,管本大队必要的宣传工作。说来也巧,七O年三线建设时的指导员这时仍旧担任大队书记,叫汪绪仁,是个深得人心的好书记,是他仍旧要我做大队的资料员和宣传员,具体工作是及时发现好人好事,以快板、顺口溜、简讯等文艺形式进行报导表扬。同时对消极因素也要提出批评(一般不指名道姓)。总之通过各种手段,营造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千方百计提高工效。 记忆中当年国家没有出台劳动法,上阵人员无年龄限制,凡有劳动能力者都动员上工地。也有自告奋勇上前线者,我队就有两名十三岁少年上了工地,一男一女,男孩长得白白胖胖,结结实实颇有力气。女孩小巧玲珑,蹦蹦跳跳,尖尖的嗓子,快言快语,劳动很卖力。其实这女孩家庭条件好,就是有书懒得读,偏要请缨上工地,大家给她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布娃娃!这对金童玉女充满活力,积极肯干,各使着一把小锄头,为上土能手。成了工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再加上其他未成年的男孩女孩,他们这档人被称为“三八六一”部队,为乌江改道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事例我都及时通过广播一一作了报道、表扬。指挥部动员所有学校师生分期分批上工地慰问劳动大军,表演各类文娱节目,我则将工地的好人好事转达给大队小学,也让其编排成文娱节目,在工地表演,通过观赏各项慰问表演,驱除疲劳,提高士气。 整个工程建设实行工日任务制(也叫定额,可单兵,可合伙,视情而定),土方计立方或计担数。石头则规定每劳动日单挑一千斤,双抬二人共一千五百斤,视运距而定。 施工期间,上级要求和当地群众搞好关系,所有的住户们都从方方面面给我们提供方便,腾出最好房间给我们住宿,下班后为我们烧水泡茶,在烧柴很困难的情况下还给我们烧火暖身子,哪怕是烧稻草。我们则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尽力报答各自的住户。比如挖出的乌江故道地下的树木,有些用今天科学的眼光看,埋蔵年份很久的树木(柳树、槐树等)纹路清晰,质地坚硬,可能不少形成了乌木,只是当年不识货罢了。在木材非常困难的当年,我们都一点不漏的带回到各自的住户,住户们真地利用其做了小家具,剩下无用处的作烧柴。施工中还发现大量草炭,化验证明草炭是上好的肥料。第二年我们队还组织劳动力挖回了几拖拉机。 苦战到隆冬,整个河道被开挖改直完毕,连下游的潘家湾石头山嘴巴也被爆破开挖成河。两边河堤下部修成两米来高的平台,以防河水冲刷导致河堤崩塌,平台以上再建筑符合设计要求的河堤,第二年组成专业队采石护坡。河道挖通后,封闭沿河大小缺口,引水归河,保障第二年农田的春耕用水。接近过年,各大队还把分给的废河还田任务在顶风冒雪的情况下如期如质完成。 河堤修好后,在陶主任的筹划下,整修了偕东公路(偕乐桥至东鹜山)。修起了东鹜大桥,曾经的县委书记,当时的益阳地委书记杨世芳以毛体笔法题写了桥名:东鹜大桥。破天荒地使各种车辆能顺利开进东鹜山。异地建设还使不少男女青年谈成了对象,我所熟知的就有三对,他们的婚姻一直稳固,现在都是三代同堂的幸福之家。 当年参战人员大多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从修黄材水库,宁灰公路,到修三线铁路,修洞庭渠道和公社大队的各型号水库,社、队公路,年年都未停歇过。时至今日当年的这类人群至今年龄都有七、八、九十岁,年龄最小的也有六十几岁了。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并未享受今天的甜美日子而成了作古之人。他们可都是建设祖国的功臣啊。在艰苦的环境下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我想这支屡战屡胜劳动大军的劳动目的,决不只是那每天仅几毛钱的劳动报酬,而是希望国家和人民记得他们的功劳,更渴望得到表彰和传承他们那代人的精神。他们的功劳和品德可歌可泣,不应该被后世人遗忘。 作为与共和国同龄的本人,亲历亲为了各个时期的生产生活,对当年的状况刻骨铭心。形成了想要为当年的建设者们歌功颂德的心结,如今趁我还有一丝能力之时,真心想以文字记录一下当年艰苦奋斗建设祖国的真实片断。起到安慰生者,告慰亡灵之目的。致敬为共和国改天换地,为人民造福的老一辈劳动者!英雄们战天斗地,流血流汗,功高至伟!劳动光荣!人民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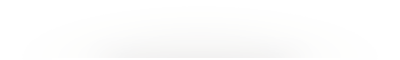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